查良镛怎么读,哪句经典的话让你忘不掉?
答 | 江隐龙
“我偏要勉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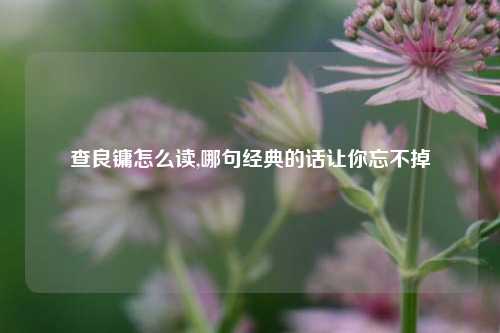
熟悉金庸武侠的朋友大约能猜到这句话是谁说的了。没错,这正是《倚天屠龙记》中,赵敏看到心上人张无忌已经要与周芷若成亲时说的说那句话。当时张无忌、周芷若双方的宾客均已列座,双方拜堂在即,赵敏曾经的师父范遥也如此劝她:“郡主,世上不如意事十居八九,既已如此,也是勉强不来了。”而赵敏便是这样回答的:“我偏要勉强。”
故事的结局最终是张无忌离开了周芷若,最终与赵敏走到了一起。但在赵敏去“搅局”的那一刻,她所面对的却是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刻。她身处一群对自己抱有极大敌意的人中间,目睹着昔日情人与其情敌的婚礼,在别人大喜的日子里做着最不合礼的事,换作任何人,恐怕都不会也不敢如此理直气壮。
而赵敏,却做了,也做成了。没有那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搅局”,赵敏的前途虽广,却再没有她想走的路。于是这个险冒也得冒,不冒也得冒。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
中国传统文化说惯了中庸之道,知足常乐,强扭的瓜不甜就连任逍遥的庄子也说出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样的话。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却不敢说原来凡事可以勉强,原来不知足也有不知足的乐,原来强扭的瓜也可以很甜。为什么不能以有涯随无涯呢?如孟子所说的“掘井九轫不及泉”,但依然不甘心做一口弃井,尽然要努力搏一搏的人生,难道会不幸福吗?
当豫让几度刺杀赵襄子未遂,最终求拔剑刺赵襄子之衣以示复仇,最终吞剑***时,这种勉强不动人么?当诸葛亮之一次北伐失败的时候,写了后《出师表》,表中提出了六个“未解”,但依然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勉强不感人么?当中国人在“最危险的时候”,还要“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时,这种勉强不鼓舞人么?
很多变局,很多希望,就开始在“我偏要勉强”这句话上了,这是那些天天只会念叨“知足常乐”,只会等而下之的人所不能明白的道理,这其中也自然有那些人所不能体会到的乐趣。他们更不明白的是,向上的路只会比向下的路要好走,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勉强过。
为什么有人觉得武侠小说没落了?
真正的武侠小说还要看金庸,古龙那个年代,也就是七十到八十年代。
那年代武侠小说作者真是人才辈出啊!先有粱羽生新派武侠缔造者写的《萍踪侠影》《七剑下天山》等等著作,脍炙人口的大作引起了不小的凡响。
再后来就有了武侠小说的大家,金庸,和古龙俩位了。
金庸原名查良镛,浙江人氏,后来***香港,创办了《明报》又在其创办的报纸上刊登自己写的武侠小说,没想到一炮走红,其影响力己遍布世界华人圈,引起了一股武侠小说热潮。
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缔造者,金庸是把武侠小说推向巅峰的实际施行者。可以说在华人圈里,无论是七八十岁的垂暮老人,或者是十多岁的年青人都是金庸的书迷。
记得,我们那时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偷看金庸武侠小说的岁月,常常是看着看着,欲罢不能。书中荡气回肠的情节。主人公不断的离奇遭遇,以及高超的武功都是看的是热血沸腾,仿佛自己化身于男主角,驰骋于江湖,快义恩仇,侠义滔天。
金庸先后写了十四部小说,基本部部都是精品。
《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鹿鼎记》等等都是让人欲罢不能的武侠大作。
再说说古龙,一个后现代的武侠巨匠,古龙小说没有年代感,而是把江湖恩仇,兄弟义气,美女,美酒写在书里,成就了一招致敌的大侠,也把江湖侠士的快意人生写的是活灵活现。
古龙小说里更多是快。李寻欢的飞刀快,阿飞,西门吹雪的剑快。常常是银光一闪,喉咙己出现一个血洞。
陆小凤的灵犀一指快,常常用他两根指头就能夹住,对手的武器。
古龙小说里的铁拳,木剑甚至飞花掂叶都是杀人利器。
古龙和金庸比起来,古龙是后来者,但他创造出了另一种形式的武侠风格。
还有卧龙生,陈青云,温瑞安等等作家都是那时候武侠小说的大家。
进入二十一世纪,武侠小说已是青黄不接了,没有真正意义上出现一位大家。只有出现了一位黄易,算是一位优秀的武侠小说创作者。
向是他写的《大唐双龙传》《寻秦记》《大剑师传奇》都是可读性比较强的著作。
现在流行的是快餐文化,网文,玄幻系列,而真正的武侠精品己经绝迹了。武侠小说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了,而且比起金庸,古龙是差之甚多。
而且作品是浮夸之多,玄而又玄,生涩难懂,读起来看几行就看不下去了。
这可能是我们七零,八零后和现在所接受的教育和观点不同,对那些
所谓的武侠网文根本没有兴趣看下去。
言归正传,那么武侠小说真的落伍了吗?我觉得确实是落伍了,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武侠精品小说。
作者的青黄不接,以及作品少之又少,更具有影响力的武侠小说更是没有了。
有人说《雪中悍刀行》是一本好的武侠小说,可是我看了几页,却怎么也看不下去了,比起金庸古龙的小说,还是有差距的。
我也是个爱看武侠小说的人,好的书经常看,确实也碰不到了像金庸,古龙写的那样精品的武侠著作。
只能把他们的隔一两年翻看一遍,以让我的江湖梦重温一遍。
快餐文化的兴起,或许是真正的让那些精品武侠小说成为永远的精典。
总结:武侠小说是真正的没落了,那些精典己成为永远的记忆,而想超过这些精典恐怕是难之又难。
金庸为什么封笔?
说金庸先生为什么封笔,还得从他的小说创作历程谈起。传统武侠到了梁羽生手里,有一个讲究,就是人物一定要是正义、爱民爱国的,所以梁羽生写的武侠用四个字可以概括,家国天下。金庸早期基本继承了这一写法,而且发展了这一写法,甚至塑造了这一种类型人物的巅峰----郭靖,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射雕英雄传》郭靖塑造这一人物秉承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理念,但是,这种人物是有缺陷的,这种人物的特点就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红,要么是身负家仇国恨,要么是出身名门正派,它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不苦大仇深,不根正苗红怎么办?或者名门正派不那么正怎么办?中国人讲,得意时学孔孟,失意时学老庄,金庸探索了一条新路,创造了一种新型武侠形象---道家武侠,给了失意的武侠人物一条出路,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之一个尝试的是杨过,《神雕侠侣》中的全真教并不那么伟光正,杨过虽然也有襄阳的壮举,但走的一直是避世的路子,对他而言,最理想的地方莫过于终南山古墓。相对于传统的武侠来说,他没有了那么多家国天下的束缚,而开始追逐内心,杨过的特点就是至情至性,当然杨过这个人物还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如果不是他悲惨的童年,这个人物简直可以用讨厌来形容。《神雕侠侣》杨过但是,金庸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塑造出了令狐冲这个人物,达到了道家武侠的一个巅峰。令狐冲从不想做英雄,也不想做高手,即使他成了一代高手,想的也是逃避,但是令狐冲的逃避并不是弱小,在传统文化里,邦无道则隐,既然事不可为,独善其身就是更好的。《笑傲江湖》令狐冲道家的侠,也有一个困境,那就是侠客退隐了,那些逞凶的奸邪如何处理。《笑傲江湖》的结尾,其实已经隐藏了这种疑问,金庸的选择是让奸佞小人们纷纷作法自毙,这样的结局虽然不能说坏,但是却给人意犹未尽之感,我们不免产生疑问,难道真的能一逃了事吗?换言之,儒家之侠参与政治,道家之侠逃避政治,参与也好,逃避也好,都是政治的一部分。金老先生毕竟高才,早在《神雕侠侣》之后,他就开始了另一种探索,佛家之侠。之一个这样的侠客是张无忌,张无忌看起来懦弱可欺,但却是直面问题的,那就是对于仇人和奸邪都是可以用善良和佛法化解的,在《倚天屠龙记》里,连成昆这样的大奸大恶都不是一杀了事。《倚天屠龙记》张无忌值得一说的是,佛家武侠的形象,一直到《侠客行》的大粽子石破天发展到了一个顶峰(当然并不是说石破天超越萧峰),石破天的无名无功,无我无人是佛家审美的极致。《侠客行》石破天但是佛家之侠的困境在于,从张无忌开始,都难免给人软弱可欺的印象。所以射雕三部曲伟大之处在于,三部书的男主角,正好是儒道释三家不同哲学的体现。但是相应的问题也因而产生,对于武侠,金庸之前的作品已经是巅峰之作了,他很难在做突破。但金庸毕竟是金庸。他再一次突破自我,创造了反武侠的经典人物,韦小宝。而金庸之所以封笔,也正是因为《鹿鼎记》。《鹿鼎记》韦小宝在《鹿鼎记》里,金庸推翻了所有武侠形象,达到了武侠小说创作的巅峰。在这里侠义没有了任何出路,要么如陈近南那样为宵小所戕害,要么如归辛树那样蠢不自知,要么像冯锡范那样为人驱使,在这里,侠义被戳得千疮百孔。不惟侠义,盛世、明君、忠臣、良将、大儒、高僧同样在这里粉墨登场,又在这里被暴露得体无完肤。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来了个总曝光,这里只有无尽的灰暗破败,只有韦小宝这个没有任何侠义精神的小混混身上反倒有了一些闪光。
所以我们可以说,金庸用韦小宝给自己一手创建的江湖打了个粉碎,就此封笔。
金庸和古龙谁的成就高?
众所周知,金庸先生和古龙先生是中国现代小说历史上两大不可抹灭的擎天柱,成就之高,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金庸先生笔下的郭靖、杨过、小龙女、黄蓉等等人物世人皆知,传遍街头巷尾。古龙先生更是不差,小李探花--李寻欢、林诗音、小鱼儿、花无缺等等人物亦是闻名于大江南北,为无数子民口头传诵,津津有味,乐此不疲。
那么,在这两位神人之间,到底谁的成就更高呢?
金庸先生的文道一向从容,朴实,隽永。反观古龙先生,有所差别,自属紧峭,抒意,淋漓。
金***从容有一个特征就是多用二字词、四字词句,每句话多为偶数字,读起来就显得平和,悠然,有些简单就像骈文一般四言六字。例如:
《鹿鼎记》“北风如刀,满地冰霜。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北而行。”又如:
《笑傲江湖》“和风熏柳,花香醉人,正是南国春光漫烂季节。福建省福州府西门大街,青石板路笔直的伸展出去,直通西门。一座建构宏伟的宅第之前,左右两座石坛中各竖一根两丈来高的旗杆,杆顶飘扬青旗。右首旗上黄色丝线绣着一头张牙舞爪、神态威猛的雄狮,旗子随风招展,显得雄狮更奕奕若生。雄狮头顶有一对黑丝线绣的蝙蝠展翅飞翔。左首旗上绣着“福威镖局”四个黑字,银钩铁划,刚劲非凡。大宅朱漆大门,门上茶杯大小的铜钉闪闪发光,门顶匾额写着“福威镖局”四个金漆大字,下面横书“总号”两个小字。进门处两排长凳,分坐着八名劲装结束的汉子,个个腰板笔挺,显出一股英悍之气。”
但金老先生写得还是脱胎于传统文学的武侠,他的小说也难免受到骈丽的格式的局限。但他的小说仅从其形,不从其朽气,人物与情节都居有新的思维和发展。因此,金庸的小说比之梁的更有生命活力。
金庸这个思想的巨人的浓缩在于他那通过虚拟夸张的浪漫叙事透视现实人生的苦乐真谛和借光怪陆离的江湖传奇展示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的近九百万字的武侠小说中。
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作者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而是通过对金庸小说形式和语言的论述,来探讨金庸小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萧”和具有雅俗弹性的主要因原。
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到如今,金庸小说的流播已经冲出华人世界,走得更远。但是,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要一时说清却是很难的,在这里,我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前辈说书人常说“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我觉得用这一想法作为指导思想来切入金庸作品涵盖乾坤的殿堂无疑是有效的。
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郭靖、黄蓉、令狐冲、杨过、小龙女、乔峰、韦小宝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欧阳峰、灭绝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谈完金庸先生,接下来不妨说说同样是功成名就的古龙先生。
古龙先生的小说不是注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回顾,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古龙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体验,他常用细腻的笔触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贵独立的人格,以此来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在古龙小说中,多写变态人格,追求外化怪异人物性格的刻画,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诞、神秘、孤僻、行事固执,自尊心强,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种子。这种情况可能与古龙的身世、心境、经历有关。
再次顺道说说金庸先生的这方面。
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
忽然小弟想起了梁羽生,想必大家对这位小说家也不会陌生。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但人物性格单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
谈到小说情节,古龙武侠小说也和梁羽生、金庸小说有明显不同。三位大家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引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梁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前工后拙,开篇十分吸引人,以后的情节则渐趋平淡,显得有点才气不足。金 武侠小说恰恰相反,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示,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干巍峨,枚叶繁茂,宠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魄,回肠荡气。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炉火,小说情节犹如炉火上的一壶水,火越烧越旺,水越来越滚。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又不相同。他的小说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情节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着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计中套计,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折。
刚才将上述作了总结,以下便是论文的形体。
众所周知,金庸先生和古龙先生是中国现代小说历史上两大不可抹灭的擎天柱,成就之高,威名之大,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先说金庸先生,其笔下的郭靖、杨过、小龙女、黄蓉、张无忌等等人物世人皆知,传遍街头巷尾。古龙先生更是不差,小李探花--李寻欢、林诗音、花满楼、陆小凤、楚留香等等人物亦是闻名于大江南北,为无数子民口头传诵,津津有味,乐此不疲。
论文风,金庸先生的文道一向从容,朴实,隽永。反观古龙先生,有所差别,自属紧峭,抒意,淋漓。两者各有千秋。
金***的从容有一个特征,就是多用二字词、四字词句,每句话多为偶数字,读起来就显得平和,悠然。有些简单就像骈文一般四言六字。例如《鹿鼎记》之中:“北风如刀,满地冰霜。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北而行。”
再看古大侠的文体,也很是独特。例如《天涯明月刀》就是一部彻底的诗化小说,可称先锋作品,将对后世造成巨大影响。
但金老先生写得还是脱胎于传统文学的武侠,他的小说也难免受到骈丽的格式的局限。但他的小说仅从其形,不从其朽气,人物与情节都居有新的思维和发展。因此,金庸的小说比之梁羽生的更有生命活力。当然,古龙先生与金庸比肩,亦是分庭抗礼,不相上下。
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到如今,金庸小说的流播已经冲出华人世界,走得更远。
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
而古龙小说最注重的则是人性的体验,他常用细腻的笔触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贵独立的人格,以此来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在古龙小说中,多写变态人格,追求外化怪异人物性格的刻画,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诞、神秘、孤僻、行事固执,自尊心强,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种子。这种情况可能与古龙的身世、心境、经历有关。
一本小说,文笔固然重要,但重中之重的还是剧情。
谈到小说情节,古龙武侠小说也和金庸小说有明显的不同。两位大家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引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具体而言,金庸武侠小说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示,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干巍峨,枚叶繁茂,庞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魄,回肠荡气。
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又有所不同。他的小说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情节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着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计中套计,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折。
总结的说,两位武侠大作家成就至今无人可攀比。重要的是,他们优秀的作品给予了人们在劳苦生活的同时,有那么丝丝清凉,渗入人心。
小弟不才,且对古龙研究不深,今日也仅是投机取巧罢了。
古龙逝去较早,因此了解他的人也不多,远远低于金庸。此刻在下便对古龙先生做一个简介。
古龙,原名熊耀华,著名武侠小说家。约1937年生,祖籍江西,幼年迁居台湾。父母离异后,古龙以半工半读和朋友资助的方式继续学业,后肄业于淡江大学(英文专业)。他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纯文学作家,但最终却走上了武侠创作的道路。
古龙的武侠小说创作始终秉承“求新求变”的宗旨,在2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他以超凡的想象力、深厚的文学底蕴和锐意变革的创新意识,突破前人窠臼,赋予武侠小说新的生命,使之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上。近半个世纪以来,古龙凭借《多情剑客无情剑》、《楚留香》、《陆小凤》、《七种武器》、《绝代双骄》、《欢乐英雄》等多部脍炙人口的经典小说,非但征服了亿万读者,深远地影响到后来者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影视改编热潮,长时间风靡中国乃至东南亚各地,历久不衰。而古龙亦由于在这些方面的巨大成就,被誉为与金庸并驾齐驱的两大武侠宗师。时至今日,仍有许多武侠、奇幻小说在重复模仿古龙的路子,更有不少影视作品,借古龙的金字招牌,不断创造收视***。
与誉满天下的古龙小说相比,古龙影视同样魅力非凡。上世纪70、80年代的港台电影界就有“楚原+古龙+狄龙=卖座”的说法,古龙作品的改编电影也多次获得亚洲影展及台湾金马大奖,如根据《武林外史》改编的电影《孔雀王朝》就让楚原于1979年获亚洲更佳动作片导演奖,徐克崛起江湖的处女作电视剧《金刀情侠》亦改编自《九月鹰飞》。更有甚者,上世纪相当长的1段时间内,歌星在东南亚登台,若不演唱《小李飞刀》一曲,观众便会大喝倒采。而郑少秋等主演的《楚留香》系列电视剧当年在各地热播时万人空巷的盛况,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90年代根据《流星·蝴蝶·剑》改编的《莲花争霸》与《剑啸江湖》,则奏响了中国乃至亚洲武侠剧颠峰时期的最强音。
古龙很早就尝试电影与文学的互动,如将蒙太奇笔法及结构运用到武侠小说,开辟了武侠创作的新天地;又从事编剧,并自创宝龙影业,把武侠文学的独特意韵与曲折故事带入电影,最终成就奇情武侠电影上世纪数十年的辉煌并深远影响几代人。古龙作词、施孝荣演唱的民歌《侠客》,意气风发,豪情万丈,被誉为词曲唱3绝,是台湾80年代大热名曲。实际上,古龙为“武侠美学”理念的形成与“武侠文化”的推广作出的巨大贡献远不止此,其成就在中国的文学界与影视界都堪称伟大。金庸小说的深度,体现在作家对具体历史文化问题的理性思考,读者获得的理性启迪,是一种理性的深度;古龙小说的深度,则体现在作家对人生残酷性纯然感性的把握,读者获得的感情冲击,是一种诗性的深度。
古龙为人真诚,慷慨豪迈,不拘小节。美酒、佳人和阅读是他更大的爱好,但古龙最看重的,还是朋友。古龙博览群书,这为他的武侠作品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丰富的内涵;古龙又风流多情,他交往的女性虽多,但无一不是彼此吸引,真心相待;古龙交朋友更是率性而为,肝胆相照,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常常呼朋引伴,纵酒狂歌。古龙是寂寞的,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纷扰矛盾的世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古龙又是幸运的,无数朋友和读者通过酒和书跟他走到了一起。1985年,病中的古龙因再次酗酒导致食道破裂,使原本就欠佳的身体雪上加霜,最终借酒解脱,于9月21日走完了他多姿多彩的传奇人生,享年48岁。
为此,我深深的,感到惋惜···
金庸先生的小说就如同一杯奶茶,中西合璧,中国小说的笔法和骨架,欧美文艺的神韵。故事内容热闹,却总有一股避世之气
古龙先生的小说开创了新的武侠写作手法,除绝代双骄外,其他小说所写内容相对金庸先生的作品,要散漫许多,有些段落更是废话连篇,故弄玄虚,甚至已经影响了其某些作品的可看性。不拘小节的性格造成其作品紧凑度不够,留下了更大的遗憾
金庸先生笔下的人物绝大部分都如游戏一样慢慢练级,群艳垂青,最终功成身退
古龙笔下的主人公则往往是一上来就很强大,处处留情,犹如种马一般,时时喝酒,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度量很大,气概非凡。
要说而今小说界,太多青年的脑子、思想被那些毫无营养的 *** 小说占据,深陷其中。多的是那些都市暴力、色情,无所不有,也对青少年们一点利处都没有,只能凭空***人们的大脑,但却会令你的思想浑浊。
我很愤怒,现在的少年不懂得如何去欣赏金庸、古龙两位***的作品,反而一再贬低,去推崇那些个“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的小说。按说那两位当红 *** 作家的作品的确可以消遣,却绝对比不上看金、古两人的作品来得更加愉快。
《诛仙》一书的风格离而今普通的 *** 小说较远,更可以说略学得了金庸先生小说的皮毛之处(在这里说一下,本人拥有一本《诛仙》书籍,在这本书的后面有大家的评语,看了之后真是哭笑不得,不禁叹然那些人不知好歹。你瞧他怎么说,说萧鼎的成就***已大成,这般下去,岂会在金庸等人之下?!这“金庸等人”是泛指金、古、梁众人,那家伙竟是不知天高地厚,那萧鼎和金庸先生一比高下,真是可笑,可悲,可叹呐!)
相比其他 *** 小说而言,个人是非常喜欢诛仙的。常听见他们说《诛仙》一书枯燥乏味,缺乏***。这点我同意,诛仙和黄书一比的确是没有任何***可言······呵呵,想必大家懂我的意思,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让你在一年的时间写一部20万字的小说?
虽说是个假设的问题,仍然走一波热情,毕竟一百万元写二十万字的小说,平均一字五元,这样优厚的稿酬,是现实中的大神才配有的待遇。
二十万字是一般网上长篇小说的更低字数,对于日更起码三千才能拿全勤奖的写手来说,简直是小儿科,信手拈来,就是一百万写一千万字,也不知有多少人求而不得。虽然日更两三万字的超级作者并不多,但四五个人组队夺金就容易多了。
那些号称日更上万年年写几大部的头部大神,365天全年无休码字并不困难, *** 小说求量不求质的环境下,也难免有替补写手的嫌疑。对默默无闻的小作者来说,为人作嫁衣裳,是看得起你。郭德纲的电影《祖宗十九代》的主角就是影子作者。
但若以茅盾文学奖或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来要求就难了,这需以短篇的精良来写长篇,好比以拍电影的节奏来拍电视剧,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不过二十余万字,耗费时日时不说,数度修改只余原稿三分之一多一点。一个段子是福楼拜的朋友早上去他家,问写了多少,他说写了一个逗号,晚上又问他,福楼拜说,他把写好的逗号擦掉了。
大作家有文思泉涌的时刻,也有只字难挤的煎熬,倚马可待的天才毕竟是少数。写作是高级脑力活动,不是抄课文赶寒暑假作业,一蹴尔而成之。
老话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那是写诗,孔子曰"郁郁乎文哉?"讲得是写文章,洋洋洒洒的长篇小说若出精品,才值百万身价,想来绝非易事。
罗曼•罗兰46岁的时候开始,花了他20年的时间,一个男人最黄金的时间,成熟与精华来写120万字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他说:“成败对我来说,都无所谓,问题并不是要取得成功,而是要服从内心的命令”。所以它不仅仅只是一部书,而是作者的信仰,关于一个音乐天才与自身、与艺术以及与社会之间的斗争史。
即便看在一百万的百分之一份上,元元也写得出二十万字,至于流量质量难保证,能不能获奖,这个就敢保证不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