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代将领,推荐出对明朝贡献更大的十个人?
的确,个人说个人话,关于“贡献更大的十个人”,完全是不可能有所谓“公论”、定论的,我就举出我熟悉、尊敬的十位明代的名臣、名将(不列帝王)。
徐达徐达是真正的“将将之才”(对应的是“将兵之才”,当然,不仅只有这两个概念),作为明初统一战争中的主要统帅,他败陈友谅、张士诚,北伐元朝,屡战北元,可谓是开国之一功臣,《明史》编者便有感叹道:“中山持重有谋,功高不伐,自古名世之佐无以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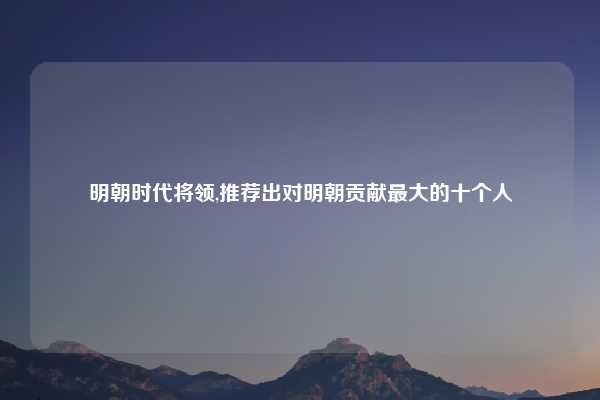
【徐达】
三杨三杨是明朝初期三位杨姓名臣的合称,分别是“西杨”杨士奇、“东杨”杨荣、“南杨”杨溥,他们三人历仕明初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六朝,自最早入阁的杨士奇算起,他们在内阁共有四十余年(杨士奇年龄最长,入阁最早;杨荣其次;杨溥入阁最晚,资历最轻),对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的影响尤为巨大,开创了“仁宣之治”。史称“自正统前,三杨硕贤,继世迪德,海内晏安,人相忘于治平之间”(唐枢·《国琛集》)、“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焦竑《玉堂丛语》),成为了明朝贤相的“代表人物”。
【谢环《杏园雅集图》,绘“三杨”等群臣】
胡濙、魏骥胡濙堪称是明初的传奇人物:长在礼部为尚书(三十二年)、享寿极高(八十九岁)、家门和睦(到老仍是如此)。而他又是联系惠帝朱允玟和成祖朱棣的关键人物,正是他十数年的遍寻天下,才解开了朱棣的心结。
魏骥之所以被我提到,不是因为“冷门”,也不是因为他的政绩、高行,而是他的年龄,历数明代诸多***,年最长者,首推魏骥(九十七岁),即使放眼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帝国”,也少有大臣能望其项背(少数有高允、王恕等)。
于谦于谦以干吏、廉吏之名,早在“土木之变”前便已声扬朝中。英宗被俘后,他又力撑危局,与群臣拥戴郕王朱祁钰为帝,组织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剌入侵。局势稍定后,他又劝朱祁钰迎回英宗。主政时,以身作则,廉洁奉公,拔擢人才,并创团营制度以影响有明一代之军制。更重要的是,于谦作为一代忠烈之士的典范,上继文天祥、余阙、方孝孺等人(各有争议,此处搁置),影响后世数百年,“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于谦画像】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一首《石灰吟》,便已能证明这位大臣对后辈的激励作用了。
杨廷和杨廷和作为早负“神童”之名的饱学之士,不仅没有沦为方仲永之辈,反倒一跃而起,扶摇直上,官拜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成为内阁首辅。他是武宗末年及世宗初年的政坛中的核心人物,计除宠臣,总揽朝政三十七,兴革百事,成就了帝位更迭中的平稳过渡,也为世宗朝的恢复作出了杰出贡献。《明史》赞其“诛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功在社稷,即周勃、韩琦殆无以过”,确是盖棺论定。
【杨廷和像】
王守仁王守仁作为一般人认为的“完美”人物,实现了稍微“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即使有再多的争议,但仍不能否认王氏将心学一脉发扬光大,使其成为明代一支主流学说,影响了现在的华人地区及东亚日、韩各国。
【王守仁半身像】
在军事上,王守仁平宁王宸濠之乱,定西南思田、诸瑶、断藤峡叛乱,剿南赣盗贼,于当时明朝的稳定亦有重要贡献。后人对他推崇者极多,有“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王文成公为明之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等诸多论赞。
戚继光戚继光对于军制改革的贡献,一般人即使不了解,也能说上两句。他一生戎马,以世袭武将,南驰北征,先在东南抗倭十余年,又于蓟辽筑边十余年,善于结交权臣,以贯彻自己的主张,改良军阵、武器,加强边防,可谓是古今以来将帅中的杰出者。正是因为他于戚家军及前前后后的军民的努力,东南沿海才免于崩溃,黎民得以安生,堪称“千古不朽的豪杰”(黎东方语)。
【戚继光塑像】
明朝的五军都督府是个什么衙门?
五军都督府由明初大都督府发展而来,1361年,朱元璋设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事。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为防止军权过度集中,废除大都督府,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五军都督府各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
明朝立国之初,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很大,各都督不仅负责管理卫所的训练与生产,还参与明朝的军事决策。后来,朱元璋为防止将领专权,撤销五军都督府调兵权,将军队调遣权收归皇帝;兵部在军队中虽有任免、升调、训练之权,但不统兵。每逢战事,由皇帝临时委派专人担任总兵官,统率卫所部队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归还将印,军队归还卫所。
1449年,土木堡之变中,大批重要军职人员阵亡,使得五军都督府无法有效组织京师防御,于谦所领导的兵部,开始负责总督军务、掌握兵戎、总兵之权。土木之变之后的景泰时期,于谦既掌握兵部的军权,又掌有五军都督府的军队指挥、管理权,五军都督府的权力绝大部分转移到兵部,这一过程也体现了明代武将和文臣军权的消长,之后五军都督府职权日益衰微,直到明亡。
明朝有名的将军都有哪些?
明王朝早期的伟大将领有,徐达,常遇春,傅友德,邓俞,汤和,沐英,蓝玉,李文忠,燕王朱棣,张铺,大将军李如松,李成粱,戚继光,卢文照,孙传庭,熊庭弼,左良玉等等,还有二臣吴三桂,祖大寿。
明朝时代将领军挟如何辨别?
10普通士兵9伍长8高级伍长7百夫长6千夫长5校尉(分步兵和骑兵)4普通将军3卫将军(禁卫军的)2大将军1皇帝从九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侍诏、满洲孔目、礼部四译会同官序班国子监典籍、鸿胪寺汉鸣赞、序班、刑部司狱、钦天监司晨、博士、太医院吏目、太常寺司乐、工部司匠 文职外官;府厅照磨、州吏目、道库大使、宣课司大使、府税课司大使、司府厅司狱、司府厅仓大使、巡检、土巡检 武职京官:太仆寺马厂委署协领 武职外官:额外外委 未入流: 文职京官:翰林院孔目、都察院库使、礼部铸印局大使、兵马司吏目、 崇文门副使 文职外官:典史、土典史、关大使、府检校、长官司吏目、茶引批验所大使、盐茶大使、驿丞、土驿丞、河泊所所官、闸官、道县仓大使 武职京官:无 武职外官:百长、土舍、土目军与兵并存,是明代独特的军事制度。顾炎武指出,“判兵与农而二之者,三代以下通弊。判军与兵而又二之者,则自国朝始”。目前学术界对明代军兵的研究,存在着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即认为兵即是募兵。这样,军与兵的区别就在于召募、是否世袭了。而实际上,军与兵在组织形式上的不同,是军与兵的根本区别。 军属卫所,由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卫指挥使、都指挥使,上而至五军都督府统辖。卫所军及官世袭,仅五军都督府官及都司不世袭,为流官,由世职卫所官及武举选授。卫所军及官属军籍,携带家属,世居一地,并代代相传,基本上不再变动。每一卫所的驻地固定,军士数额固定,将官设置亦有定例。总之,卫所制下权力分散,兵将分离。但景泰以后,兵部权力上升,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夺五府之权,五府官变动虚衔。 兵属营,由什长、队长、哨官、把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统属,直属兵部。兵一般不世袭,但由卫所***为兵者例外。兵无户籍的规定,兵服役期限不长,一般不终身服役,多战时创设,事毕汰兵撤营,但在重要的军事防御卫则常川戍守。营兵不随家属,更接近现代兵制。营伍官无品级,有者则是卫所制下的官品,无定员,不世袭。营兵与营将相习,战时不需要朝廷任命,直接由总副参游统带出征。将权相对提高后,兵可由将自行召募,召者与被召者关系密切,甚至在主将发生变故时,兵即散去。 军与兵在饷给形式及数量上也不相同。军饷由屯田解决,屯田废坏后,补以盐课及民运,后亦部分取给于京运年例。而兵之粮饷全数取足于京运年例银,或加派之新饷。数额也不相同,兵有安家、马价、衣装、器械等银,月粮也较丰厚,而军只有月粮,战时或出征时才有行粮。 军与兵在使用上也不相同。兵渐渐取代了军的作用。兵主战,军主守、主屯。“兵御敌而军坐守,兵重军轻,军借卫于兵,壮军乃复充兵”。但兵并没有彻底取代军的地位,卫所制一直到明朝灭亡。清初改卫所军为屯丁,部分保留了漕军的职能,卫所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才彻底消失,而卫所作为一个地理单位而行政管辖机构取消的时间则更晚。 明营兵制与卫所制官职常有同用之情况。一般(不很严格)地说,总兵、副总兵由公侯伯等勋臣及都督等官充任,参将、游击多由都指挥使等官充任,守备、把总则由卫指挥及千、百户充任。 洪武年间的48卫所还只是一种备操编制,到永乐以后72卫所的五军营和以前在性质上有所区别,不仅是备操编制,同时还是战斗编制,如永乐八年以后的北征。 参将、游击将军等职,早已有之。太祖北伐之时就在正将军、副将军下置,为出征体制之常设官(常以总兵加将军衔之举)。只不过明初出征之兵常由卫所调发,待中叶以后营兵制成,乃分两途,殊不为怪。 明中叶以后卫所军逃亡甚大,正统二年九月兵部统计,天下都司卫所逃亡军士达120万人,相当于全国额定兵员的一半左右。而至正德,据兵部尚书王琼估计卫所逃亡数已占额数的十之八九。逃亡者多为精壮,未逃者尽是羸弱,故卫所军毫无战斗力,不难理解。 镇戍兵的营制看来没有统一,从总兵到把总均可独立成营,人数参差不齐,编制规模悬殊。
明朝的将领为何需要家丁打仗?
明朝中后期明朝将领的家丁是军队中精锐之中的精锐,最典型的是辽东的李成梁,李成梁招募家丁,组成自己的私人武装,是当时辽东军队中打击东北少数民族各部落的最强武装力量。1593年,万历朝鲜战争中,明将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就曾经率领“家丁”发起碧蹄馆之战:
癸巳朝鲜之役,平壤大捷,李如松以平殄在迩,不欲他兵分其功,潜率家丁二千人夜至碧蹄馆,遇伏一举歼焉。其家丁李友升者,积劳已至副总兵,只身殿后战殁,如松始得脱。
发起碧蹄馆之战的是李如松的家丁发起,目的是不想让其他将领们分功劳,家丁有2000之众,而且李如松的家丁战斗力远高于他所属部队的战斗力。其中李如松有一个家丁叫李友升的人,因为功劳升为副总兵,正是因为他的殿后死战,李如松才在战役中脱身。
家丁不在明朝官方的军籍,而是将领们招募的各种精锐力量,是自己私人最拿手的“特种部队”,因此在一些重要战役中,反而是“家丁们”冲锋在前。(明朝四大卫所之一的威海卫略图,四大卫所分别是天津卫、威海卫、金山卫、镇海卫)
朱元璋的尴尬——卫所制的崩塌。明朝的卫所制度是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军屯制度而兴起的一种军事制度,军队士兵是屯田者,也是军人。朱元璋制定卫所制度后曾经自豪的说:
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卫所制度中最重要的是军户制度,士兵是世袭制度,很难摆脱军籍。军户主要来源于元朝原来的军户以及明建国后的一部分军人户籍,后来一部分犯罪充军的罪犯也被编入“军户”之中。
一军户中正军一人,余丁一人,携带妻子儿女赶赴卫所,军队分给军士房屋、土地,每月提供粮食补给。卫所中的士兵一部分人耕种田地,一部分服役,轮流耕作农田,农田的一部分收获上交卫所,供给军需。这就是朱元璋所谓养兵100万,不让百姓花费一粒粮食的卫所制度。
卫所中军人及其家属的生活非常困苦,一般要远离家乡的卫所服军役,水土不服,逃兵非常之多。洪武三年,据记载有逃兵47986人;1438年,逃兵达到163万人之巨大(包含家属)。(《荡寇风云》中戚家军剧照,戚家军是募兵制招募的士兵,而非卫所中的士兵)
一切的一切源自于明朝军队军官的贪腐,很多给卫所士兵的月粮不能按时给付士兵,军队行军也只发给口粮,其他服装自备。到了明宣宗朱詹基的时,卫所的军官私自占有军屯土地,将军屯中更好的土地拿到手中,经常让士兵耕种军官们的土地,而且已经常态化。士兵和家属们面对这种困苦状况,那还有心思在军中服役,很多军人举家逃亡。再者,朱棣北伐蒙古之后,明朝的对外战争很少有规模大的,军队的重要性下降了,明朝皇帝们也不太关注军队建设,军人的社会地位也下降了很多。
到了嘉靖皇帝时期,很多卫所中军籍士兵逃亡者达到70%;到了万历年间的后期,卫所军籍中士兵逃亡达到80%,很多重要的边关卫所,军籍士兵只有50%在岗了。
朱元璋吹嘘的卫所制度在军官们的贪腐下土崩瓦解了,卫所军队战斗力直线下滑。(李如松像)
明朝募兵制和家丁制的兴起。如同唐朝开始的“府兵制”在唐玄宗时期改为“募兵制”一样,朱元璋的卫所制度也遭遇了现实的尴尬。嘉靖皇帝时倭寇横行,卫所的军队不堪一击,于是大明朝开始了“募兵制”。
募兵制不同于原来的军户制度,士兵的人身比较自由。卫所制度中,皇帝和内阁、兵部掌握了军队的实际权力,但募兵制则必须下放权力给各级具体负责的将领们招募士兵,军队的权力已经下移了。
明朝的将领的家丁制度随着募兵制的开始而迅速升温。明朝弘治年间曾经有人上书称:
辽东总兵、副总兵、参将、都指挥、千户等官,先年各选骁勇军士随从杀贼,久之遂为家人。其升调官员则有带去军丁,见在世袭子孙有参将以下者、一家有十余姓,一姓有十七八人,又有隐占军丁、从令使嫁者。
这是巡抚辽东官员的奏折,明朝边关各级将领都蓄养了不少家丁,这些家丁不在军籍,姓氏也五花八门,随着将领们的调动而调动,成为将领们的私人精锐武装,开始时将领的家丁人数是比较少的,后来逐渐扩大,譬如记载中李如松的家丁队伍有2000之众。
家丁们的主要来源是那些人呐?主要来源于卫所中的士兵,一部分卫所中的士兵最早成为卫所军官们的佃农;一部分家丁则是军官挑选卫所中精锐的士兵进入;一部分是社会上招募的勇士。抗倭名将俞大猷曾经招募了30多人进入自己的家丁队伍,这些人擅长水战。家丁原来多是卫所中的士兵,属于明朝 *** 养的兵,这样一来成为卫所军官的私人武装。(万历朝鲜战争碧蹄馆之战图,冲锋陷阵的是李如松的家丁们,军队中的精锐)
原来卫所中的士兵逃的逃,挑选后只剩下了老弱病残,战斗力非常低下。
明朝的统治者对此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万历年间,军队将领的家丁们已经合法化了。家丁和所依附的将领是一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将领们也把自己的家丁们培养成了军队中的精锐,擅长攻坚克难,为将领们获得战功和利益。
1630年,吴三桂率领二十多个家丁,在几万后金军队中救出了自己的父亲吴襄,可见吴三桂的家丁犹如他自己培养的特种部队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