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宿池边树 僧敲月下门,柴门夜永有僧敲?
花圃春残无客到,柴门夜永有僧敲
《声律童蒙》中的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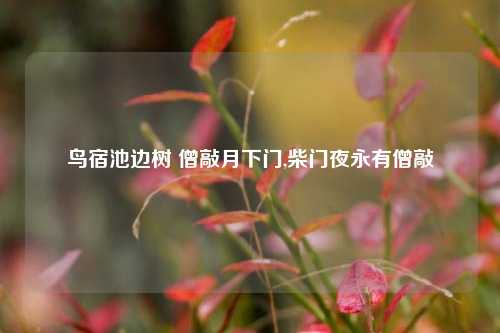
上联源自[唐]白居易《微之宅残牡丹》诗句:“残红零落无人赏,雨打风吹花不全。”
下联源自唐代诗人贾岛的名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夜永:即永夜,长夜。
唐朝有个诗人名叫贾岛,专注苦吟,人称诗奴。有一年他到长安赶考。途中,他在驴背上吟诵起不久前写的两句诗。
他觉得其中一句“僧推月下门”的“推”字不够生动,想换成“敲”字,但考虑了很久,仍然难以取舍。于是,他反复吟诵着,一会儿做推门的手势,一会儿做敲门的动作,街上的行人还以为他得了神经病。
忽然迎面来了一队车马仪仗,原来是长安府尹韩愈出巡。路上的行人都急忙向两边回避。只有贾岛仍然骑着毛驴走在路中央出神地做着推敲的姿势,结果被鸣锣开道的差役们一把揪下驴背,提到府尹大人的轿子跟前问罪。
贾岛这才回过神来,赶紧伏拜在地解释说:“我只顾在驴背上吟诗,没听到回避的锣声,因此冒犯了大人,还请大人恕罪!”
韩愈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听说贾岛因作诗入迷,才冲撞了自己,也不禁为贾岛的专注所动,于是用温和的语气问道:“你做了首什么诗,念来听听。”
于是,贾岛把这首五言律诗一字一句地念了一遍:
《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末了,贾岛还向韩愈请教:究竟用“推”字好,还是用“敲”字好呢?韩愈非常赞赏他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并建议把“推”字改为“敲”字。
韩愈说:“从意境的角度看,山中夜晚,寺门紧闭,题目又写‘幽居’;在那月光皎洁、夜深人静的环境中,忽然听到几下‘梆梆’的敲门声,以动衬静,就更显出寺院的深幽沉寂。而用‘推’字就显不出这许多好处来。”
贾岛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用“敲”字。后来常用的“推敲”一词,即来源于此。
岛初赴举京师?
贾岛初次参加科举考试,住京城里。 “推敲推敲”,为唐代著名诗人贾岛吟诗炼句的故事。贾岛,字浪仙,苑阳(今河北涿县)人。作诗非常注意锻字炼句。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引《刘公嘉话》栽。岛初赴举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练之未定,遂于驴上吟哦,时时引手作推敲之 势。
时韩愈吏部权京兆,岛不觉冲至第三节。左右拥至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云云。愈立马良久,谓岛日:“用‘敲’字佳矣。”
这个故事在《唐诗纪事》、《隋唐嘉话》中都有记述。成语“推敲”的出典,就是由于这个故事。“推敲”亦作“推敲推敲”或“推敲字句”,用以形容写文章反复地研究,斟酌字句。也有用来作对问题多方面考察、研究的。
作者使用推字还是用敲字?
关于僧人归寺是用“推”还是用“敲”字,缺乏必要的背景交代。旁观者只能做臆测:
如果是一个单人住持的小寺庙,和尚自己管理、自进自出,那他自己最了解情况。如果出门前,他当初是自己把门虚掩上了。再回来,自然用“推”比较合情合理。敲门有什么意义呢?敲给谁听呢?
如果是一个大的庙。就像今天许多大的单位一样,僧人因自己的杂事耽误了回寺的时间。时间晚了,正常情况下,看门人应该从里边锁住了寺门,那么自然就应该用敲。作为老员工,自然之道自己单位的规矩、知道寺庙开门锁门的时间规定。所以回来晚了,既然门已经从里面上锁,应该是敲门。“敲”字为宜。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游方的僧人去“投宿”:到别人的庙里边临时借宿。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更应该使用“敲”。因为按常理说,正常情况下夜晚都是要锁门的。既然是里边已经锁住,那么还是“敲”为好。总不好随便推开别人家的门,推门就进吧?既然是求人,总得有起码的规矩和礼貌吧?这种情况下,他的“敲”还应该是有节制的、声音不能太大,客客气气、彬彬有礼的“敲”才对。理直气壮的砸门,强迫对方必须打开门,总不合适吧?
据传说,当年韩愈和贾岛交谈以后,停下车马思考了好一会,对贾岛说:“用‘敲’字更好”,给他拍板儿决定用“敲”。可见他们两人的交谈,韩愈是了解了贾岛的那个诗句的上下文,即前面的背景情况的。由此逆推,大概是一个比较大的寺庙,有管理制度,里边儿已经锁住,僧人个人原因耽误了回程,要敲门等里面的人给他打开门。
另外韩愈作为一个诗文大家,应该更多考虑的是诗文的意境。试想:寂静的夜晚,如果是僧“敲”月下门,那么寂静夜空当中就会有声音恰到好处的传出。给诗作的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别有一种意境、别有一种情趣;一静一响,有相映成趣的美感。所以诗文大家确定用哪一个字,恐怕也有从意境、美感角度出发的考虑。
题李凝幽居贾岛注音版?
原文:
闲居少邻并, 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 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 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 幽期不负言。
注音版如图:
一个孤僧独自归全诗?
一个孤僧独自归,关门闭户掩柴扉。 半夜三更子时分,杜鹃谢豹啼子规——罗嗦诗趣谈。
罗嗦诗是杂体诗的一种,又名重复诗。它是有意堆叠同义词,故意重复,造出一种甚有诗味的意境,表达一种幽默效果。
诗歌固然要求语言凝练,但重复罗嗦以至成诗,也自有其趣。
据冯梦龙的《古今谭概》一书记载,北宋雍熙年间,有位自称“诗伯”的人曾写过一首题为《宿山房即事》的诗:
一个孤僧独自归,关门闭户掩柴扉。
半夜三更子时分,杜鹃谢豹啼子规。
此诗乍读,文字流畅,音韵和谐,很是有几分“诗味”。可仔细一读,便发现诗中废话连篇:诗中的“一个”、“孤”、“独自”都是指一个人,“关门”、“闭户”、“掩柴扉”指同一个动作,“半夜”、“三更”、“子时”指同一个时间,“杜鹃”、“谢豹”、“子规”指同一种鸟,其俗名是布谷鸟(布谷鸟的知名度很高,尤其在我国,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很多人都知道它。“布谷”是鸣声的谐音,对其叫声,农民译为“布谷布谷、快快
播谷”,旅者译作“归去归去、不如归去”,庶民翻成“阿公阿婆、家家好过”,母亲把它当作哄孩子之声:“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单身汉则说是替他们诉苦:“光棍真苦、光棍真苦。”)。
全诗四句二十八字所表达的意思其实仅用十二个字就可以表达清楚:“孤僧归,掩柴扉。半夜时,杜鹃啼“。但仔细琢磨琢磨,这种重复“啰嗦”有着一种绝妙的表达效果:它把这个和尚内心的孤独感刻画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与之异曲同工的是,后人也依葫芦画瓢写了这样一首“奇诗”,啰嗦得很可爱:半夜三更子夜归,关门闭户掩柴扉。爱***子老婆问:你是那个何人谁?实际上,只用“半夜归,掩柴扉,老婆问:你是谁?”即可说明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