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真迹,米芾为什么大骂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等书家为丑书之祖?
米芾曾批评颜、柳书法淡而无趣,丢失了古法,说他们的书法是丑书。米芾批过颜、柳,批过欧阳询,还说要“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米芾对书法先辈的批评毫不客气,有人说米芾这是学成了艺骂师傅,我倒觉得米芾对书法前辈的这些批评具有重要意义,米芾始开了中国书法批评之先河,对米芾批评前人书法的行为,我们应从正面意义上去理解,并对其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予以肯定。
米芾根据什么对颜真卿等人的书法提出尖锐的批评呢?米芾自幼年起,就学习欧阳询、颜真卿和柳公权等人的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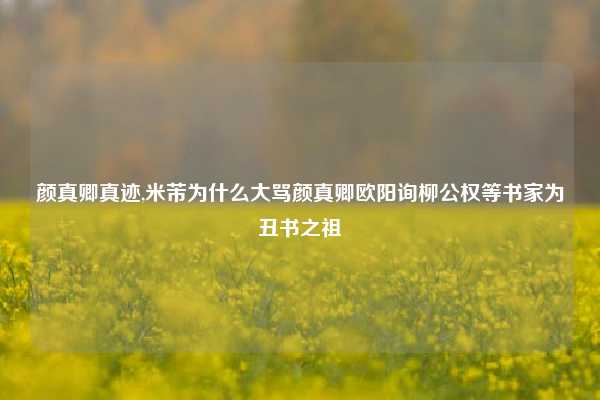
“初学颜,七八岁也。字大至一幅,写简不成。见柳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
米芾对“欧、颜、柳”等人书法非常熟悉,对他们书法艺术中的优与劣也十分清楚。可以说,米芾对他们书法的批评是建立在十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的。
米芾认为“欧、颜、柳”的书法没能很好地传承魏晋风韵,整齐平正有余,却缺少率真情趣。从艺术应发乎自然,表达率真情感的角度来看,米芾对欧、颜、柳等的这种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也是客观的。因为没有什么艺术作品是完美的,有其长,也必有其短,在赞美其长时,也别忘了指出其短,并规避之,要做到有所取舍,这是对艺术经典学习品鉴应有的正确态度。米芾用尖锐的语言指出了欧、颜、柳书法艺术上的缺点,这种批评是正面的,有积极的意义。
艺术作品创作出来以后,就要任人品评,只要不对艺术家进行人身攻击,单纯的在艺术领域内评价其优劣,那怎么说都完全不应该存在问题。褒也好,贬也罢,各种观点都是建立在自我对艺术的审美与认知之上,对一件艺术作品有不同的看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那怕这件艺术品有多么的经典,都不应影响我们对其以挑剔的目光来打量审视,并提出我们的质疑与看法。
艺术的发展永远离不开艺术批评,艺术永远是在“否定之否定”中生存与发展。书法是艺术形式中的一种,在书法艺术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也是引导书法艺术不断前行的灯火。
前些日子,笔者品评唐代书法名家颜真卿的经典行书《祭侄文稿》时,有很多人留言讨论,其中有一些留言竟然对笔者品评艺术经典的行为进行人身攻击,有人甚至将艺术与其它东西联系到一起,简直令人无法理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虽贵为经典,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对其无限制吹捧的理由,再好的艺术作品也有缺点和不完美的一面,我们为什么没有面对指出这些艺术经典缺点与不完美的承受力?为什么要将对艺术心平气和的品评,变成一蹦多高的激烈怒怂,好像指出了经典的不完美之处就是对经典的亵渎?
一七八四年,歌剧《费加罗婚礼》在巴黎首演,其作者,著名作家博马舍希说想听到最真实的批评,他说:“如果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毫无意义”。他的这句话后来成为经典,被广为传颂。我觉得在我们的书法评论中,博马舍希的这句话更具有现实意义。
米芾在九百多年前对书法前贤所做的尖锐批评,并未引来当时人们对他的种种非议。而在时下,对古代书法经典的评论,却常常会引来各种异样的目光或是轻蔑地言语,有人会说:“那是经典”。潜台词是经典是不能挑毛病的。甚至还有人说:“你能写上来吗?”言外之意是,你没有写出艺术经典的能力与水平,你就不配拥有自已的观点,你就被剥夺了品评经典的权力,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品评书法艺术毫无疑问需要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对书法艺术的认知也需要达到一定高度。但这不等于说我评价王羲之的书法,就需要拥有和王羲之一样的书法水平,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对古代的那些书法家的作品只能是顶礼膜拜了,连馆阁体都得当成葵花宝典来学习了,也就谈不到有所取舍了。
米芾是一代书法名家,他对书法艺术有深厚的积累与实践,他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已所洞察出的前人书法中存在的弊端,我认为米芾这种做法比那些无限制的吹捧,言不由衷的赞誉要胜强百倍。无节制、无底线的虚情赞美大肆泛滥,对书法艺术的发展百害而无一利。而这种情况曾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中的常态,在中国古代的书法评论中,极度夸大的,甚至玄虚化的描述与赞美之词屡见不鲜,从东汉的蔡邕,再到唐代的欧阳询都曾在书法论述中,以夸大、玄虚的用词来描绘笔法,什么“刚则铁画、媚若银钩…仿佛兮若神仙往来,婉转兮似曾伏龙游…”等等,不胜例举。
而米芾对此现象深恶痛绝,他亦曾直言不讳地说:
“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无益学者”。
而古代书法评论中对前贤的赞美,更是极尽言语夸大之能事,苏轼在赞美颜真卿时竟冠之以“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之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来评价。在那个对书法先贤一片赞美之词的时代大环境里,米芾却保持一份独有的尖锐与冷静,这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书法批评,米芾对欧、颜、柳书法的批评令人对他们书法中的存在的缺点与弊病有所警醒,而后世对米芾书法的批评也有同样的作用,明代书评家项穆也曾批评米芾书法之弊端:
“米之猛放骄淫,是其短也”。
米芾批欧、颜、柳及二王,后人亦曾批米芾,这些一针见血的批评使书法艺术得以良性发展,所以说:书法艺术不能缺少批评!
古诗四帖到底是不是张旭的作品?
张旭传世的书法就那么几件,而且多无落款,尤其古诗四帖,因为诸多因素,更加扑朔迷离,历来说法不一,争议不断,难辨真伪。
一、无落款。
二、南宋之前,误认为是谢灵运所书。
三、仅凭董其昌认定为张旭真迹,延续至今。
四、谢稚柳、启功等权威人士,都有评说,亦真伪意见不一,缺少有力证据。
五、“丹”、“玄”之说,版本很多,一说避讳谢灵运祖父谢玄,庾信将“玄水”、改为“丹水”;一说避讳唐玄宗之名,将“玄”改为“元”。
六、张旭所传的经典草书作品,大都难辨真伪,而且风格不一,无从比较。
时隔千余年的今天,恐怕更加难以辨别此帖的真伪,即使专业权威人士也无从考证。
其实,对于是否真迹,与我辈习书者而言,并无多大实际意义,无论真假,都不影响它在书法史上,独一无二的大草经典之地位。
为了更好地理解此帖风格,我们可以把古诗四帖与张旭的其它草书作品作一比较分析:
般若波罗蜜心经:如同古诗四帖,也是一件真假有争议的作品,甚至有人认为出自王羲之之手。此作草法如行楷,法度谨严,字字交代清晰。都说张旭性格豪放,近似狂颠,而他写此心经,非常理性,感觉不到丝毫的狂野。点画以篆隶笔法,方圆并举,提按、使转明显,结体紧密,而笔势取斜视,纵横奇生。通篇节奏没有大起大落的起伏。
肚疼帖:这也是一件传为张旭所作。寥寥数行,节奏非常自然,气贯意连。有评论说,是张旭肚子痛不可堪,无心之作,似有道理。既无古诗四帖“矫情”,也无心经之谨严,点画笔法婉转自如,似云烟缭绕,神奇意趣皆盎然,而不失法度。
千字文:千字文虽非真迹,为翻刻碑石,而通篇气势可谓一泻千里,时而横云断山,时而长驱直入,姿态狂颠,最符合张旭草书风格特点,如果是真迹,应是张旭草书最杰出之作。
而古诗四帖,通篇草法不如心经严谨,不如肚痛帖自然,不如千字文的气势。笔法上不如心经果断,不如肚痛帖细腻,不如千字文丰富。但它如一笔书,笔法松弛,笔势婉转而跌宕起伏,轻重、疏密、呼应等节奏变化丰富,参差历落,字字连贯。
它也有不足之处,例如笔力时有飘弱之感,通篇的章法,与跌宕起伏的字势不相称,缺少节奏上的自然变化,这与肚痛帖的气贯意连之章法,有明显不足。
了解这些特点,才是真正明白此帖真伪的关键所在。
请问大家觉得什么是书法?
书法是书者学习历代名家吸纳其精华形成自己风格的作品。书法可以修身养性提高自信!
大家见过欧阳询的行书吗?
歐陽詢的書法在唐四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特別是他的楷書《九成宮》名氣最大,成為後人學習的經典法書。他自創的歐體學派與顏體、柳體和褚體皆不同,他是初唐時期最著名的書家,尤其㕥楷書傳世。縱觀他的行書同樣不失一代大家的風范,他的行書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行為,應該介於亦行亦楷二者之間,我認為有㕥下個特點:1、布字謀篇舒朗。有云“密不透風,疏可走馬””說的就是字與字之間、行與行之間都留有一定的空間,而歐陽詢的行書正好契合上面的“疏可走馬”之詞。2、字的橫畫要比他的楷書《九成宮》裏字勢向右上傾斜更甚,就是右肩提高在3一6度之間,而不是一般說的橫斜2一5度,他敢於打破固有橫斜的模式和窠臼,與同代人有不一樣的思維。3、他的行書可以說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行書,應該是“兼行兼楷”更准磪些。4、從行書的字裏行間處處顯示歐字的結字特點和用筆轉換的風格,不用注名,一看字就知道是歐字書法。以上是自己的看法,歡迎大家評論。
薛宝钗是否算貌美如花?
薛宝钗称的上美貌如花,至于琴棋书画则未必精通。
先来看贾府诸人是如何评价宝钗的容貌。
第六十三回,诸芳夜聚怡红院,为宝玉祝寿,宝钗抽到的花签上画着一支牡丹,题着“艳冠群芳”四个字。众人看了都笑说:“巧的很,你也原配牡丹花。”
宝琴等人初到贾府,宝玉见过宝琴之后,回到怡红院中,对袭人等说:“你们还不快看人去!谁知宝姐姐的亲哥哥是那个样子,他这叔伯兄弟的形容举止另是一样了,倒像是宝姐姐的同胞弟兄似的。更奇在你们成日家只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你们如今瞧瞧他这妹子,更有大嫂嫂这两个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了。”
以上是大观园里与宝钗接触最密切、以女性为主的人对宝钗容貌的评价:艳冠群芳,绝色的人物。
元春省亲,“见宝林二人亦发比别姐妹不同,真是姣花、软玉一般。”这是元春作为女性,唯一一次与宝钗见面时对宝钗容貌的评价:姣花软玉一般。(或者可以说姣花单指宝钗,软玉特指黛玉,姣花一词已足以阐释元春对宝钗容貌的赞赏。)
兴儿对尤二姐尤三姐说:“奶奶不知道,我们家的姑娘不算,另外有两个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无双。一个是咱们姑太太的女儿,姓林,小名叫什么黛玉,面庞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这样的天,还穿夹的,出来风儿一吹就倒了。我们这起没王法的嘴都悄悄叫他‘多病西施’。还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儿,姓薛,叫什么宝钗,竟是雪里堆出来的。”这是一个男性远观宝钗对她的容貌做出的评价:天上少有,地下无双。
第二十八回,元春赐端阳节礼,宝玉与宝钗的礼物一样,其中都有红麝香珠。在贾母屋里,宝玉请求瞧瞧宝钗的红麝串:
“可巧宝钗左腕上笼着一串,见宝玉问他,少不得褪了下来。宝钗生的肌肤丰泽,容易褪不下来。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到:‘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他身上。’正是恨没福得摸,忽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
这是宝玉作为一个男性,近距离的观看宝钗后对她的容貌做出的评价:妩媚风流。宝玉与宝钗接触的多而近,宝钗的容貌尚令宝玉“不觉就呆了”。
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也不论是远观还是近望,亦不论是乍看还是常阅,宝钗在众人的心中都是美人儿。宝钗的容貌经得住多方位的检验,称的上是貌美如花。
宝钗涉猎广泛,知识渊博,但她不一定精通琴棋书画。
宝钗小时候读过《西厢记》等杂书,当黛玉接鸳鸯的牙牌令时说出“良辰美景奈何天”与“纱窗也没有红娘报”,便立刻知道出处。她生日那天,为了迎合贾母,点了一出《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宝玉嫌点的戏太热闹,她随口就能将戏文的韵律之美及词藻之妙娓娓道来。宝玉出现悟禅机端倪,黛玉欲令他“收了这个痴心邪话”,拷问宝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宝玉答不上来,这时宝钗细诉六祖慧能接替五祖弘忍衣钵之典。
宝钗的博学强记还不仅仅表现在对杂书、戏文、佛典的熟稔上,她对医学也颇有考究。第四十五回,宝钗探黛玉,说起黛玉的病症来,宝钗说:“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健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铫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这是她对药性、药理的见解,颇合食疗养生之道。
宝钗的海棠诗、螃蟹诗、柳絮词均拔得头筹,也见其在诗文创作上的不凡能力。
第四十二回,惜春奉命作画,宝钗提出三大要素:一,分宾分主,添减藏露得宜;二,界限比例适宜;三,高低疏密恰当。
接着又详细列出作画所需的油粉大案、各号画笔、各色颜料等材料,林林总总,周全细致。
宝钗让宝玉帮助惜春,如遇难以安插之处,好拿出去问问那些会画的相公。如果宝钗精通作画,大可以自己指点,又何须舍近求远,让宝玉拿出去请教别人。她就好比某些诗词评家,知道作诗词的要素,也知道哪些诗词高妙,但是自己却未必能写出千古佳句来。真要作画,她也许还不如惜春。
宝玉在探春生病的时候,赠送过一副颜真卿的真迹给她。探春的屋里摆放着“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森林一般。”看大观园里各屋中的陈设,唯有探春与书法最紧密。观前八十回,没有发现宝钗与书法的关系,可见这并不是她的强项。
周瑞家的送宫花,来到王夫人的屋里,彼时迎春和探春正在窗下围棋。六十二回,林之孝家的向探春回话,探春正和宝琴下棋,宝钗和岫烟在一旁观看。第二十三回,宝玉初入住大观园,“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这是前八十回里与下棋有关的文字,宝钗只有一次观棋,并没有额外的展示棋技,因此不能说她的棋艺精湛。
至于琴艺,前八十回里除了提到宝玉弹琴,没有展示过任何人的琴艺,也就无从判定宝钗是否精通了。
上苍在创造一个人的时候,若不关上某扇门,必定会闭上某扇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长,也会有各自的短板。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哪怕像苏轼这样的全才,也不能说样样才学均能达到巅峰,也要受到能力的局限。宝钗作为大家闺秀,且聪慧好学,对琴棋书画不会没有涉猎。以整体实力来说,她优于众人,但也不可能样样都超出,她也会受到能力的局限。她貌美如花,颖慧好学,博识强记,温柔宽厚,哪怕未能精通琴棋书画,也是女子中的佼佼者。
